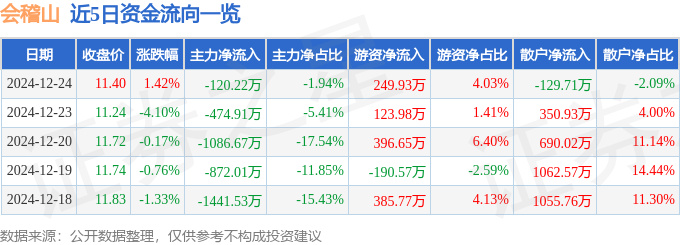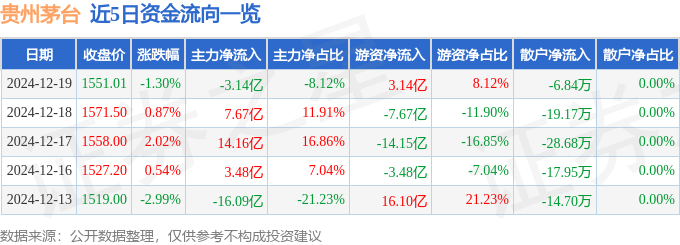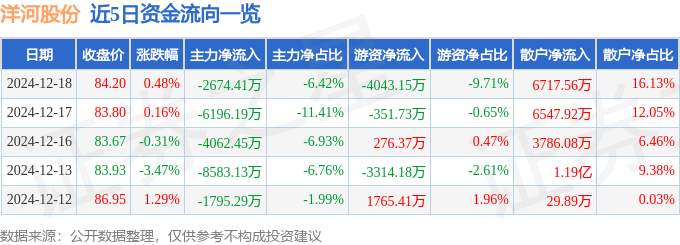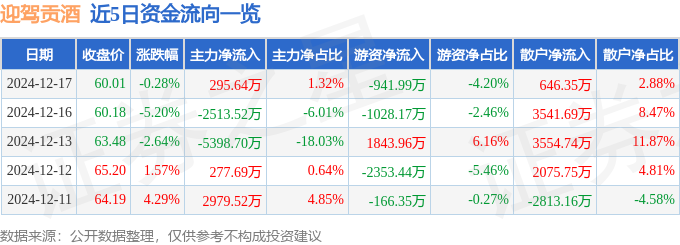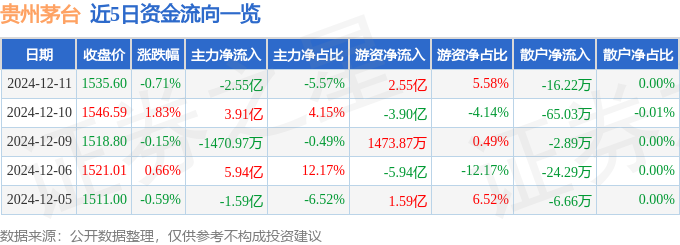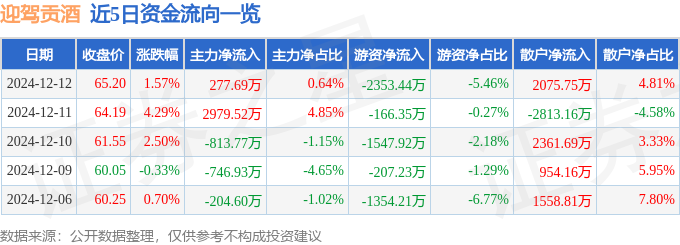我妈给他换上红衣,以俯卧的姿势埋在浴缸里,日夜尸油养之。
后来,弟弟真的活了。

我却全身腐烂,活不过当晚。
道士看出了门道。
「姑娘,你被典当走了六十年的寿命啊!」
1
我弟的尸体,在厕所里藏了七天。
那晚,他酒驾开摩托车撞飞下山崖,尸体都甩断成好几节,肠子流了一地。
我妈嚎哭完,摸黑将尸体捡回了家。
她一针一线,用慈母手中线,将儿子手脚密密缝上。
等我从外地赶回家,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
我弟早死透了,身上尸斑点点,一身血衣以俯卧的姿势埋在浴缸里。
手脚僵硬卷缩,那姿势像孩童在母体时一样。
这一幕让我脑子都蒙了。
浴缸里一缸子的血,腥臭无比,上面布满黑点,全是淹死的黑苍蝇。
「妈,为什么不报警,不下葬?」
我浑身发抖地质问。
「他……是不是撞死了人?你们不想赔偿?」
我能想到的,只有这个原因。
我弟是他们老来得子。
从小就是家里的土皇帝,被溺爱坏了,没一天认真读过书,天天跟猪朋狗友混酒吧,初中会赌,高中会嫖,是个无师自通的小恶棍。
有次强睡了隔壁村姑娘。
爸妈为了他前程,东拼西凑了十万赔过去。
妈一口咬定没撞人。
「你弟以后是要做官的,要报警了,留了案底怎么办?」她哭着拍打我。「他都这样了,你还编排他啊?」
做官,谁?
荒唐无力感充斥全身。
我妈曾笃定:「算命的说过,你弟是当官飞黄腾达的命,他才十八,离蛟化金龙还有一年呢!」
我认为他们脑子糊涂了。
「无论如何,都要入土为安,明天我会报警。」
看我坚决,爸妈互相交换了个眼神。
昏暗浑浊的灯光,让他们的表情模糊而扭曲。
离开关门时,我情不自禁地看向浴缸。
苍蝇又嗡嗡落在弟弟身上。
或许是灯光昏暗,也可能是我太过疲劳。
我竟然看到,我弟的眼皮。
轻轻动了动。
2
第二天,我被反锁在房间里。
行李手机全被扣住,我妈隔着门板说。
「大师说了,七天就能回魂,你就等着吧!」
之后几天,我每天都能闻到奇怪的热油味。
不像是猪油,一点不香,很腥臭,入骨的腥。
我妈先将半凝固的油,挖出一勺在锅里热开。
再用帕子沾上油,仔细给我弟擦拭身体。
她很细心,脚趾缝,耳窟窿、肚挤眼这些旮旯位,都会认真擦上一遍。
后来听我爸说,那是陈年老尸油,可金贵着呢。
「五年的尸油,三千,给你弟的,十年。」
「这一小罐,就得五千!」
为了儿子,我爸向来是舍得花钱的。
冬天我没厚衣服,手指长满冻疮,笔都握不住,爸妈却专门去县城给弟弟买新款羽绒服。
他们说没钱供我上高中,转头花大钱给弟弟买了「开智窍」的偏方。
弟弟吃到住医院洗胃,神婆还不认账。
「你家的文曲星全让女儿占了,儿子当然占不着了,要怪,就怪你闺女!」
自此,我每次拿到高分,爸妈脸色就难看几分。
仿佛我的成绩,是迫害弟弟不成器的铁证。
「读死书,出去有啥用,不如去打工。小睿要不是生晚了几年,轮得到你嘚瑟。」
第七天半夜,我还在睡梦中,耳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声。
我家是自建房,弟弟跟爸妈住位置好的二楼,我的房间挨着最潮湿的厕所。
我开始以为是老鼠,但下一秒,那把声音拖长声调喊。
「姐,姐姐!」
我睡得迷糊,正要回答,忽然意识到。
弟弟已经死了,谁还会喊我姐姐?
我头皮一下炸了,全身过电一样,从脚板心一路麻到头皮。
可那声音不停在厕所里喊。
爸妈赶忙开门,我弟血淋淋地杵在门口,表情木讷,眼中空洞。
我倒吸了一口凉气,弟弟竟真的活了!
「我的心肝宝儿啊,你可回来了!」
爸妈喜极而泣,也不嫌我弟身上尸臭,又亲又抱。
恐惧让我动弹不了。
我弟整个脸都是惨白木然的,他脖子僵硬转动,牙齿白森森地冲我笑。
「姐,姐!」
他在地上爬行,只是肢体不协调,像被人拆下来重组过一样。
我妈兑了藕粉,怜爱地喂他,他一张嘴。
苍蝇从里头蜂拥飞出。
我吓坏了,夺门而出。
手机还在被扣着,我只能徒步去警察局。
可没走几步,我头晕目眩,一头栽倒在地。
一股剧痛从身体里涌出,汹涌如潮水,一波又一波,有什么力量在吸走我浑身气力。
等我醒来,人已经在县医院。
我昏迷了足足三天。
这三天,没人来医院看我,医生给我做了各种检查。
「周芸是吧,你浑身器官都在衰竭,我们已经联系省里专家,可你的状况很不乐观。」
很可能,熬不过今晚。
这话犹如晴天霹雳。
我身体一向健康,怎么会突然重病?
我把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医生,可这太匪夷所思了,但医生还是帮我拨通了家里电话。
接通后,我妈矢口否认。
「谁死了?你诅咒谁呢,我儿子还好好的,就前几天扭了脚,在家休养而已。」
她破口大骂:「这丫头一天到头在城里跑,谁知道接触了什么人,现在得病了,就知道赖家里!」
我心里重重一沉。
手机里传出爸爸的建议。
「你在外头也赚了不少钱,请护工吧,你弟还在读书,过几天他十八岁过生,你也不方便回来。」
挂了电话后,我实在忍不住哭了。
也奇怪,我明明吃过太多自讨没趣的苦。
为什么,在出事后,居然还奢望他们会来关心我?
这时,隔壁床的有个道士忍不住了。
他提点了句。
「姑娘啊,你这不是普通的病。你是被人借走了六十……
点击继续阅读